诗集《大地上》于2023年7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本厚达200余页的现代诗集,以刘德稳(2007年—2022年)诗歌作为蓝本,历经1年筛选,8轮逐首修订完成。这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刘德稳整体创作风貌的精选诗集,170余首诗作精彩呈现。著名诗人伊沙、沈浩波、马非、尹马、王单单、图雅、李勋阳、韩敬源鼎力推荐。
《大地上》作为一本优秀的后现代口语诗集,作者着力书写日常生活,对大地上的人事,微小事物倾注人文关怀,洞察现代人的喜怒哀乐、精神困惑,把温暖的笔端触及到平凡人生活的各种细节之中,极力表现世间百态,用文字替卑微者发声。同时,对自我进行不断批判,显示出一个年轻诗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在孤独的彩云间淬炼自己生命的诗意
——刘德稳诗歌的艺术特征
韩敬源
韩敬源,198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出版诗集《儿时同伴》《谈论命运的时候要关好门》,现执教于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兼任丽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过去10年,当我全身心沉浸在《新世纪诗典》所构建起来的诗歌氛围中时,我以为天下的诗歌都已经很高级很现代了,这是错觉。最近两年,因工作之故,与外在的诗歌诗人接触渐多,这也包括国外当下的诗歌,更加发现并确认后现代口语诗在当代诗歌中已经走得很高很远。半个月前,也是因为工作之故,与诗人于坚首次相见,其间谈到我的老师伊沙和云南的诗歌,于老师问:“和你老师还保持联系吗?口语诗人在当下依然很孤独。”“云南诗歌我看不懂了,多少年不和云南诗人玩。”讲座中老同志依然愤然有声。我没有这么深的孤独感,因为新诗典的存在,汇集了一群对后现代口语诗有抱负的全国诗人——但是普通读者和评论家们普遍性地莫名其妙地对口语诗的回避和漠视甚至嘲讽也是存在的事实,也不是非要去辩去争获得认可,我也读过两天《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瞬间便释然了——别去想入世的热闹,幸福地在孤独中创造辉煌。没有最忙,只有更忙,除非我放掉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并忍受在此地养娃谋生的不易。学生刘德稳来电邀请为他的新诗集《大地上》写一篇,我正在写工作总结;左右催赶紧给读者购的书发货,我正在布置疫情防控,愧疚地回复左右说:“长安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总结。今天没发出你就跟我绝交!”遥想当年我出第一本诗集的欣喜若狂如在昨日,自己的优秀弟子要出第一本诗集,必须写——师傅怎么待我这个徒弟的,我不能把这个优良传统丢了。
在云南写后现代口语诗,不但孤独还“危险”,周围有一群写口语化抒情诗的官方诗人,从教18年“发现”的几个弟子也散落在这个大环境中。刘德稳孤独得都要哭了。说是弟子,也是朋友,我大他4岁。2005年我从西安外国语大学辞别伊沙到丽江任教,还担任班主任,刘德稳是第一届学生。当时毫不起眼的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我也不知道我的诗歌对他影响会这么大。大概在他毕业后的3年,一个正准备放暑假前的日子,抱着一瓶白葡萄酒专程从昭通来到丽江,仅只为陪我喝一口。
一、享受孤独并桀骜着为微小的生命显影歌唱
后现代口语诗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为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生命显影歌唱。我欣喜地在读刘德稳的诗歌中发现他坚守的价值。在《神秘的交接》中,他在写一个收建筑工地上铜丝线的人见到我扔垃圾时候的迫切。在《一九八六年,巴田乡卫生院大火》中他在写那些辽阔国土上转瞬即逝的悲剧。在《平民英雄》中写经营小餐馆的中年妇女的艰辛和不易。在《火灾现场》中写从大厦里抬出的都是烧焦的人。在《天坑记》中他在写那些隐没在云南群山中小如蝼蚁的人。在《一个精神病患者坐在槐树下自言自语》中写那些生病而活如蛐蛐的人。在《称谓》中写云南农村中人的群像。我很欣慰刘德稳把自己的诗歌美学投向这些转瞬即逝而显得卑微的生命中。云南与风景秀丽著称于世,也就有主流希望把这里描绘成世外桃源精神领地,恰恰是后现代口语诗人在关注这些群山中的瞬间就化为泥土的人。我小时候就听过奶奶和母亲不停地跟我念叨云南人爱念叨的一句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云南人的生死观在每年夏季蘑菇从土里面密密麻麻地冒出来的时候显影,明知道吃蘑菇很容易中毒而死,但又耐不住那种致命的美味而烹而食之的诱惑。在云南,一个人死去,一个夏天就被疯长的灌木埋得找不到任何踪迹。也只有后现代口语诗才能写出这种残忍和疼痛。仔细想想,何止云南呢?刘德稳的这类诗歌,和后现代口语诗的美学追求是一致的,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丰富。但注定是孤独的,转眼刘德稳奔到40岁:“此生之路已经选定,无惧孤独,享受孤独并桀骜着为微小的生命显影歌唱,这是后现代口语诗人的荣光和辉煌!”
二、诗意提取的精湛和不惧修辞的艺术创造
刘德稳的诗歌很好地继承了后现代口语诗的纯诗之路,诗意的发现和提取非常精纯。后现代口语诗的“纯诗”是有底色的,就是人和诗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审美,我前面说到的在云南写口语诗是“危险”的,是因为一群老诗人和新出现的年轻人似乎看到了后现代口语诗“口语”表达便利华丽的外衣,完全忽视了内在的硬核,结果就变成了口语化的抒情诗,飞天茅台的瓶子里装着甲醛超标的假酒。
我说他的诗意发现和提取达到精纯,有诗为证:在他最新的一首《新世纪诗典》入选作《镰月》中:“月光穿过高楼 /从纱窗中/溜进病房/就在我们熟睡的午夜/她长叹一声/拎起九床病友的命/从弥漫着/消毒水的过道里/逃跑了。”手艺堪称精湛,在对现场的叙述和再现中,大部分口语诗人采取或者说习惯了新闻记者式的“直录”和拍照,而遗忘了艺术的创造,刘德稳出神地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修辞,月光比作人嘛,残月比作镰刀,把现代人医院中常见的一幕写得空灵而惊魂,更惊人的是寂静无声。习惯了现场直录的诗人正需要这种艺术性的创造,缺少艺术的发现和创造,口语诗就会往直白浅显,进而无味。刘德稳的本诗可以对我们的创作提供参考。

在另外一首选入《新世纪诗典》的诗歌《动静》中:“一片红叶掉在地上/哎呀一声/更多的红叶/跟着从树上掉下来/三天后/落光叶子的树/收起自己的声音/你会看见/每一棵大树上/都有一枚绿得发黑的叶子/站在高处/为冬天守灵”,同样可以看到诗意提取的精湛。场景很简单,冬天树木落叶,但是内心波澜滔天,又是一个“拟人化”修辞,万物有灵思想泛起,声色形都显于诗中,再加上云南可见的一枚绿得发黑的叶子站在高处的毫无道理的自然场景,多层滋味和诗歌之境就出来了。口语诗歌不拒绝修辞,只要你用得好,用得天衣无缝。在现场直录式成习惯的诗人身上,我甚至提倡可以适度使用一点修辞——但这个修辞的背后是人本和诗性的天然,不是故意去生造。刘德稳诗歌中的这种显著特征值得更多的青年诗人揣摩学习。
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是与刘德稳共勉,有不少的口语诗人居住生活于乡村或者文化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存在的。伊沙老师当年说我某个时期诗歌的话至今仍然有效:“不要一到云南诗歌就成植物园。”内涵上说的是口语诗歌的现代性问题。对树木有感,对生死有感,对风景有感还不够,这些领域已经被古人开垦来开垦去,很难提供新的经验和情感审美。还要对现代事物有感,对月光有感那对高铁来不来感觉?对槐树有感那对电影咖啡奶茶来不来感觉?对红叶有感对红色的口红来不来感觉?我们的感知系统也是有惯性的,过去的老事物经常来一些重复的感觉,现在的新事物通常就不来电。过去的生活形态来感觉,新的生活形态和人就经常迷茫。后现代口语诗人一定是在生活和诗上同时是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即便环境不允许也要挣扎和抗争。
三、摆脱现有的抒写话语体系寻找新的艺术生长点
刘德稳有的方面太像我了,也包括诗歌风格,几乎全部继承了我的缺点。大概在2014年,我沉浸于痛失母亲和岳父病危的漩涡般痛楚中,在江油诗会的晚间茶叙中,我的一首手艺精湛的诗得到众人的表扬。唯有伊沙当场指出:“你现在就写得气若游丝,到老年还怎么写?”受益到今天还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发出。既是对弟子诗歌的指点也是对人生的指点。在刘德稳出诗集之际,提出来与德稳共勉。后现代口语诗是人整体性的全部,单一某个方面的突出会在一时写出好诗。人性中的全部都会在诗歌中有所体现,哪里有问题,暴露无遗。所以才说口语诗是一场修行。
刘德稳的第一部诗集《大地上》整体抒写话语中整体上呈现出:死亡、疾病、月光、幻灭、虚无等冷色调的体系。这与近年来他身体有恙经常往医院跑有关,也和他所在的相对偏僻和生活际遇有关。在这个系列里,出现很多手艺堪称精湛的优秀作品,在青年诗人里写出了具有美学价值的当代诗歌,甚至比很多人的作品都出色。作为老师和朋友,每每提起我都有自豪感。但同时也有深深的忧虑,不可在此路上狂奔,不是一条长路远路。还要开疆拓土,建立自己新诗歌抒写话语体系和新的审美经验。冷色调系的诗歌强大了,生命发光发热的暖色调系的也不能弱,还要成为主项,第一流的诗人都在后者这条路上。
大部分后现代口语诗人的自我反思能力都不错,优秀的口语诗人都会自觉地增强自己的弱项。我把大家都反感的一个词用在这里:自我革命,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政治词汇而忽视之。后现代口语诗正是在不断的自我检视和反思中,获得更具生命力的艺术之路。
摆脱现有的经验和抒写话语,不停跟自己较劲,用新的审美经验丰富和治愈自己,寻找新的艺术生长点,才能在当代诗歌中留下有价值的作品。有云南《月光下的凤尾竹》和《小河淌水》的空灵,不妨再来点西北高原的雄浑热烈和壮阔豪迈,有过桥米线的清淡鲜美,也尝尝羊肉泡馍热气蒸腾的醇香。
时值刘德稳第一部诗集出版,通读其选入本诗集的优秀作品,为我的弟子和朋友高兴,其诗艺术价值追求正,技艺精湛,纯粹空灵,为后现代口语诗提供了经验和新的参考。同时也在读他的诗的过程中增强我对当下创作的深度思考。后现代口语诗每天都在生长,诗和人同理。借用刘德稳诗中之句“加固身体的栅栏”祝身体康健,诗艺精进,写出黄河之水天上来。

作者:韩敬源
网编:温清华
一审:陈鑫
二审:陈林
三审:程洪
投稿邮箱|zxxwwtgyx@qq.com
镇雄县融媒体中心
一端尽览镇雄事,欢迎下载“微镇雄”

电视新闻
更多 要闻
更多
要闻
更多
 专题
更多
专题
更多
24小时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870-3125595 | 滇ICP备 2022008061号 滇公网安备 53062702530648号
域名:https://www.ynzxnews.cn 投稿邮箱:zxxwwtgyx@qq.com
谢谢您对镇雄新闻网的关心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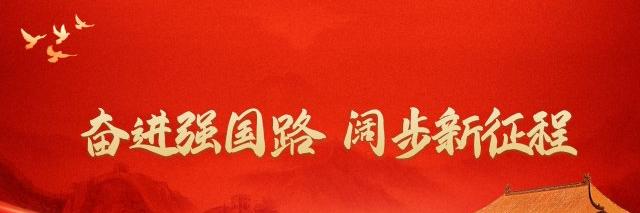
 更多资讯
更多资讯